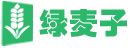1
纪念日诗章献给战争中死去的人。
但纪念的一代人也在减少和死去,
一半老朽不堪另一半也快要老朽不堪,
而谁来纪念那些纪念者?
2
一块墓碑该怎样打造?一辆汽车熊熊燃烧
在谷门 。一辆汽车烧成黑炭。一辆汽车的骨架。
另一辆汽车的残骸燃烧在另一个地方。
残骸上油着红色的防锈漆,红得
像火焰。残骸旁有一束干花。
干花结成一个纪念的花环,
枯骨构成一个枯骨复活的异象。
在另一个地方,很远,掩藏在树丛中,
一块破裂的大理石碑上刻着一些名字,一枝夹竹桃
遮挡了大部分,就像爱人脸上的一缕长发。
但每年一次那枝条被拂开一旁那些名字得到呼唤,
而蓝天下一面旗帜悬在半杆,欢快地翻卷
像一面拉到杆顶的旗——那么轻盈,那么安逸,
享受着它的色彩,它的风。
而谁来纪念那些纪念者?
3
一个人该怎样出现在悼念仪式?立正还是鞠躬,
像篷布一样坚韧还是像哭丧者一样柔弱,
像罪人一样低头还是仰首藐视死亡,
是两眼翻开像死者一样呆滞,
还是闭上眼睛就像在观测体内的星空?
而悼念的最佳时段是什么?是正午
阴影躲藏在我们脚下的时候,还是黄昏
当阴影延长,就像我们的渴望一样
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就像上帝?
4
我们在这种活动应该唱什么?从前我们唱山谷之歌,
“在贝塔阿尔法 和拿哈拉之间,
是谁燃起篝火是谁在这里牺牲。”
现在我知道是谁燃起的篝火
我知道是谁牺牲在这里。
他是我的朋友。
5
我们应该怎样哀悼?按大卫给约拿单和扫罗的挽歌,
“比鹰更快,比狮子更强 ,”我们应痛哭失声。
如果他们真的比鹰更快,
他们会高高翱翔在战争之上,
而不会受伤害。我们可以在地上仰望他们然后说:
“看那雄鹰,这是我儿子,这是我丈夫,这是我的兄弟。”
如果他们真的比狮子更强
他们还能继续作雄狮,不会像人一样死去。
我们可以亲手给他们喂食
并抚摸他们金色的魂灵。
我们可以把他们领养回家,深情地说:
我的儿,我的夫,我的兄弟,我的兄弟,我的夫,我的儿。
6
我去参加尤德的葬礼,他被炸弹炸得粉碎,
在很远的地方,一场新战争的新死者。
人们对我说要去一个新的殡仪馆:
“就在那个大奶牛场过去一点。
如果你跟着牛奶的气味走
肯定错不了。”
7
有一次我跟我的小女儿一起散步,
我们遇见一个人,他问我过得怎样我也问他
过得怎样——像《圣经》里说的。后来她问我,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我说,“他跟我一起打过仗。”
她点点头又问,“如果他跟你一起
打过仗,那他怎么没死却还好好活着呢?”
8
没人听说过茉莉的果实。
没有哪个诗人赞美歌唱过它。
人人都陶醉地歌唱茉莉的花朵,
它的郁郁浓香,洁白花瓣。
但它顽强的生命力,
像蝴蝶一样短暂像群星一样长久。
没有听说茉莉会结果。
而谁来纪念那些纪念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