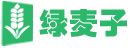整个上午我坐在学校校医室里,
数着宣告下课的一下下钟声。
两点钟,我的邻居用车送我回家。
在门廊里.我遇见父亲在哭泣——
平常遇到丧事,他总能从容对付——
大个子伊文斯说这是个严重打击。
我进屋时婴儿咕咕叫着,笑着
摆动摇篮,我感到窘迫
当老年人站起来和我握手,
告诉我他们“为我受苦而难过”,
有人低声对陌生人说,我是老大,
在学校做事,我母亲握着我的手
边咳嗽边发出无泪的气愤的叹息。
十点钟,救护车到了,运来
护士们止了血、包扎好了的尸体。
第二天早晨我走进屋去,雪花莲
和蜡烛使床榻得到慰藉。六周来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如今,脸苍白,
他左太阳穴上有紫色的血块,
他躺在四尺长的木箱里就像躺在儿童床里,
并无血淋淋的伤痕,汽车的保险杆利索地把他击
倒了。
一只四尺长的木箱,每年一尺长。
袁可嘉 译
……
我记得这个女人,她几年来
坐在轮椅里,眼睛直视
窗外小巷尽头的西克莫树
掉下叶子和长出叶子。
直截地掠过角落里的电视,
患矮树病的狂遭的山楂树从,
同样一些风吹雨淋的小牛犊,
同样一片狗舌草,同样一座山。
她稳固如那个大窗。
她的额明晰如那张轮奇的铬合金。
她从未悲叹过并且从未
携带过一盎司多余的感情重量。
跟她面对面是一种教育,
就像你跨过一道架得很结实的门——
路边斜立、干净、铁制的那种,
横在两根刷白的支柱之间,在那里你能
看见比你预想中更深远的乡村
并发现篱笆后的田野
变得益发陌生,当你继续站着集中精神
然后被那挡住视线的东西吸引住。
黄灿然 译
……
他的摩托车立在窗下,
一圈橡皮像帽斗
围住了前面的挡泥板,
两只粗大的手把
在阳光里发着热气,摩托的
拉杆闪闪有光,但已关住了,
脚蹬子的链条空悬着,
刚卸下法律的皮靴。
他的警帽倒放在地板上,
靠着他坐的椅子,
帽子压过的一道沟
出现在他那微有汗水的头发上。
他解开皮带,卸下
那本沉重的帐簿,我父亲
在算我家的田产收入,
用亩、码、英尺做单位。
算学和恐惧。
我坐着注视他那发亮的手枪皮套,
盖子紧扣着,有绳子
连结着枪托。
“有什么别的作物?
有没有甜菜、豌豆之类?”
“没有。”可不是明明有一垄
萝卜,在那边没种上
土豆的地里?我料到会有
小作弊,默默坐着想
军营里的黑牢的样子。
他站起来,整了整
他皮带上的警棍钩子,
盖上了那本大帐簿,
用双手戴好了警帽,
一边说再见,一边瞧着我。
窗外闪过一个影子。
他把后底架的铁条
压上帐簿。他的皮靴踢了一下,
摩托车就嘟克、嘟克地响起来。
王佐良 译
……
在我手指和大拇指中间
一支粗壮的笔躺着,舒适自在像一支枪。
我的窗下,一个清晰而粗厉的响声
铁铲切进了砾石累累的土地:
我爹在挖土。我向下望
看到花坪间他正使劲的臀部
弯下去,伸上来,二十年来
穿过白薯垄有节奏地俯仰着,
他在挖土。
粗劣的靴子踩在铁铲上,长柄
贴着膝头的内侧有力地撬动,
他把表面一层厚土连根掀起,
把铁铲发亮的一边深深埋下去,
使新薯四散,我们捡在手中,
爱它们又凉又硬的味儿。
说真的,这老头子使铁铲的巧劲
就像他那老头子一样。
我爷爷的土纳的泥沼地
一天挖的泥炭比谁个都多。
有一次我给他送去一瓶牛奶,
用纸团松松地塞住瓶口。他直起腰喝了,马上又干
开了,
利索地把泥炭截短,切开,把土.
撩过肩,为找好泥炭,
一直向下,向下挖掘。
白薯地的冷气,潮湿泥炭地的
咯吱声、咕咕声,铁铲切进活薯根的短促声响
在我头脑中回荡。
但我可没有铁铲像他们那样去干。
在我手指和大拇指中间
那支粗壮的笔躺着。
我要用它去挖掘。
……
凯利养了头没有执照的公牛,远远从
大路躲开:想要到那儿给母牛配种,
你须冒受罚之险,但还得照常付款。
有一回我拽着一头紧张的弗里斯兰
穿过花絮蓬松的赤杨林荫小路,
来到关着那头公牛的木棚之处。
我塞给老凯利光溜的银币,为啥
我却说不清,他咕哝一句"去吧,
到那门楼上去"。居高而临,
我注视着这做买卖似的受孕。
门,开了闩,光当当撞回到墙垣。
那非法的种畜摸索着走出厩栏,
就好象一台转轨的老火车头似的不慢不急。
他兜圈,打呼噜,嗅着。没有兴奋的喘息,
只有和气的生意人似的从容不迫;
然后是笨拙而突如其来的一跃,
他那疙里疙瘩的前腿跨上了她的腰胯,
冷漠得似辆坦克,他把生活撞击到家;
下来的时候好象一只沙袋,坠地翻倒。
"她准行"凯利说着,用木棍轻敲
她的后腿。"不行的话,再把她牵回来。"
我走在她的前头,缰绳现在松垂了下来;
而凯利吆喝着,戳打着他的非法分子:
那家伙有了空间,又回到暗处,进食。
傅浩 译
……
当你再也无话可说,那就驾车
在半岛上兜它一天。
天空高如跑道上的,
地上没有标志所以你不会抵达
而只是经过,尽管总是在绕着初见的陆地转。
在黄昏时分,地平线喝尽了大海和山岳,
犁过的田野吞下了刷白的三角墙
而你再次在黑暗中。于是回想
上釉的前滩和倒影的原木,
把浪花撕成碎片的岩石,
用它们自己的脚踩高跷的细脚鸟,
安然把它们自己驶进浓雾里的岛屿
然后驾车回家,仍然无话可说
除了现在你将用这办法解开所有风景的
密码:事物自己呈现的形状都是那么光洁,
水和地面都去到了它们的尽头。
黄灿然 译
……
任何明净的东西使我们惊讶得目眩,
你的静默的远航和明亮的捕捞。
海豚放开了,去捉一闪而过的鱼……
说得太少,后来又太多。
诗人们青春死去,但韵律护住了他们的躯体;
原型的嗓子唱得走了调;
老演员念不出朋友们的作品,
只大声念着他自己,
天才低哼着,直到礼堂死寂。
这一行必须终结。
然而我的心高扬,我知道我欢快地过了一生,
把一张上了焦油的鱼网织了又拆。
等鱼吃完了,网就会挂在墙上,
象块字迹模糊的铜牌,钉在无未来的未来之上。
……
她每天来打水,每一个早晨,
摇摇晃晃走来,像一只老蝙蝠。
水泵的百日咳,水桶的声音,
捅快满时响声逐渐减弱,
宣告她在那儿。她那灰罩裙,
有麻点的白搪瓷吊桶,她那嗓门
吱吱嘎嘎地响就像水泵的柄。
想起那些夜晚,满月飘过山墙,
月光倒穿过窗户映落于
摆在桌上的水杯。又一次
我低下头伸嘴去喝水,
忠实于杯上镌刻的忠告,
嘴唇上掠过;“毋忘赐予者”。
……
阳光直穿过玻璃窗,在每张书桌上
寻找牛奶杯盖子、麦管和干面包屑
音乐大踏步走来,向阳光挑战,
粉笔灰把回忆和欲望掺合在一起。
我的教案说:教师将放送
贝多芬的第五协奏曲,
学生们可以在作文中自由表达
他们自己。有人间:“我们能胡诌一气吗?”
我把唱片一放,顿时
巨大的音响使他们肃静;
越来越高昂,越坚定,每个权威的音响
把课堂鼓得像轮胎一般紧,
在每双瞪圆了的眼晴背后
发挥它独具的魁力。一时间
他们把我忘了。笔杆忙碌着,
嘴里模拟着闯进怀来的自由的
字眼。一片充满甜蜜的静穆
在恍惚若失的脸上绽开,我看到了
新面目。这时乐声绷紧如陷阱,
他们失足了,不知不觉地落入自我之中。
……
直立,黝黑,裹着条纹和花缎如葬礼上的
无袖长袍,鼬鼠的尾巴
炫耀鼬鼠。夜复一夜
我像客人一样期待她。
冰箱把嗡嗡声传入寂静。
我台灯暗淡下去的光波及到阳台。
小小的橙若隐若现于橙树上。
我开始紧张如窥视狂。
十一年之后我再次在整理
情书,启开“妻手”这个词
像一个陈年酒桶,仿佛它那纤细的元音
转化成了加利福尼亚黑夜的泥土
和空气。桉树那股美丽而
无用的浓烈味道说明你不在。
一口酒的后果就像要
把你呛得跌下冷枕头。
而她在那里,那只专注、有魅力、
普遍、诡秘的鼬鼠,
神话化了,非神话化了,
嗅着我五英尺以外的纸板。
昨夜一切又历历在目,就寝时
又想起你那些衣物的煤烟味,
看见你低着头,翘着尾巴在床底抽屉
寻找那件突出跳水身材的黑色睡服。
……
 扫码关注小程序
微信搜索 麦子古诗歌
扫码关注小程序
微信搜索 麦子古诗歌